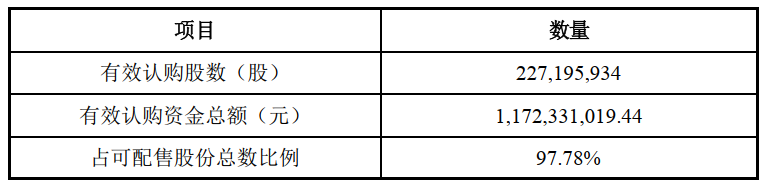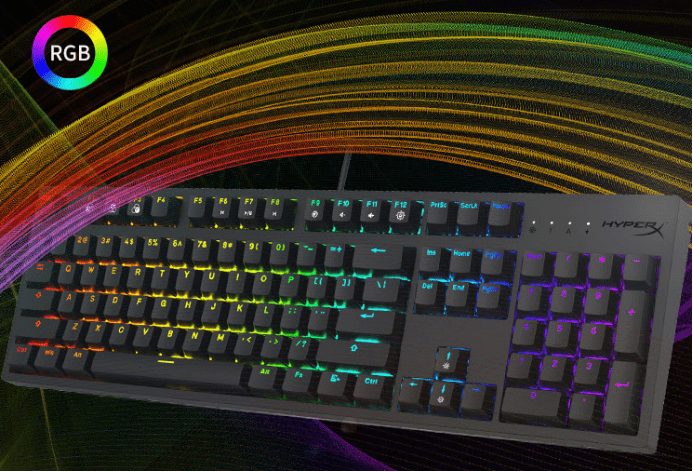◎余木匀
展览:布鲁斯·瑙曼:OK OK OK
展期:2022.3.11-6.12
地点:木木美术馆(钱粮胡同馆)
该怎么去形容布鲁斯·瑙曼?雕塑家、行为艺术表演者、装置艺术家、影像艺术家?
我们习惯用作品去为一位艺术家定性,喜爱雕塑的被称作雕塑家,擅长影像作品的被称作影像艺术家,大多数艺术家都是画家。但瑙曼不画画,按他自己的说法,他“早就放弃了绘画”,但我们会在他的作品中发现许多草图,那么这与他曾经为自己留下的结论相违背吗?事实恰恰相反,在50多年创作生涯中,瑙曼从未将自己拘泥于任何一种表达形式,从雕塑到诗歌,从影像到霓虹灯装置,他一反常态,并不像许多艺术家那样专注一种表现形式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代表风格,用一种风格,一种表现形式去概括瑙曼都不够贴切,标签化与分类法并不适用于这位独特的艺术家。
那么回到他自己说的那句话,“我已经放弃了绘画”,瑙曼的意思是他已经放弃靠一种媒介去树立、塑造一种权威性的艺术表达。绘画,尤其是架上绘画是延续了几千年的权威系统,人们很容易认为一幅油画是艺术,壁画是艺术。一些知名艺术家如杰克逊·波洛克与贾斯帕·琼斯也在反思和质疑绘画的意义,他们或以抽象的形式重构画面,或者谨慎地选择那些入画的元素,但布鲁斯·瑙曼则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彻底放弃绘画这个媒介,而用尽可能多的方式去探讨艺术的本质。
瑙曼其人
布鲁斯·瑙曼出生于印第安纳州韦恩堡,因为父亲的工作需要,他们全家不得不在中西部一直搬来搬去,这种居无定所的状态也让瑙曼从小就养成了观察环境的习惯。瑙曼以“人和他所处的环境”为主题创造了许多作品:发现我们熟悉的日常生活被忽视的一面,发现我们日常熟悉的语言陌生的一面,瑙曼的作品始终都在探索我们习以为常之物的非常态之处。
这种与主流文化几乎隔绝的状态也体现在他对专业和定居地的选择上。瑙曼毕业于数学和物理系,之后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就读纯艺术专业课程,“我一直喜欢数学的结构,那是一种严密的语言”,在艺术家的自述中,我们不难判断这种对纯粹结构性的喜爱与对语言的痴迷决定了瑙曼的艺术创作走向。
瑙曼年轻时曾在旧金山活动,并在这里找到了他对霓虹灯材料的兴趣,但他并没有像他的同期艺术家那样向往纽约和底特律这种大城市,反而搬回了美国西部。几十年来他一直住在新墨西哥州一处偏僻的农场附近,他的工作室是一个大棚屋,里头堆满电线、草图、农具和摄影及录像装置,当记者问他怎么创作时,他说当他要创作的时候再清扫出一块地方。这个大棚屋就像瑙曼脑内环境投射在现实中的艺术空间,当他需要以某种形式来创作艺术作品,他会马上行动起来,在工作室里找到需要的工具,然后开始创作。
“语言不可能被解释”
“如果我是一个艺术家,并且我在工作室里,那么无论我在工作室做什么,都一定是艺术。”瑙曼曾在访谈中如此说。他在工作室里“走路”,摆pose,甚至工作室的监控里老鼠爬过的视频也变成了艺术品。那么什么是艺术,什么是艺术品?瑙曼这个追本溯源的精神就要从他青年时期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理论的着迷说起。
维特根斯坦在自己的晚期哲学著作《哲学研究》中提到“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哲学问题”,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言形成了我们的认知边界,也阻碍了我们的认知。哲学家有理解概念的语言,数学家有理解法则的语言,很多时候我们对语言的滥用掩盖了行动的缺失,也造成了彼此间沟通的不可能。比如一个人根据自己理解说出的话在另一个人听来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们在生活中经常因为“词不达意”产生许多误解,这也是语言禁锢了我们的思维所致。
于是在木木美术馆的展览中,我们先会经过一条漆黑的走廊,走廊中布置着艺术家的声音作品《原材料》,头顶分布的音响会循环播放22条语音信息。它们都由最简单的词语组成:“Love and Die”(爱与死),“Feed me, eat me, Anthropology”(喂我,吃我,人类学),听起来不明就里。我们过分相信日常生活的语言,却发现任何试图去理解它们含义的尝试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瑙曼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理论中得到的启示。
“语言不可能被解释。”在另一件作品《好男孩坏男孩》中,我们会看见两个打扮成电视台播音员的人物在感情充沛地说一些毫无实际含义的句子,他们的专业素质令人信服,但口中说出的却是胡乱之语。瑙曼特意让女播音员播报的速度比男播音员慢一拍,以此增加了不和谐感。艺术家似乎在提醒我们,我们每天从广告和电视这种大众传媒中不停接收的是他们强塞给我们的信息,即使听起来语无伦次,我们却由于惯性依然选择相信他们说的话。
那些神秘真理
在艺术生涯早期,瑙曼创作了一系列以自己身体为“原材料”的影像作品,在本次展览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不停地把身体撞向墙角、和一根T形杆互动、模仿古希腊雕塑的姿势走路,这都是他的身体对所处环境做出的反应。“我们的环境塑造着我们,也压迫着我们”,在展览中我们会发现一条“走廊”,当一个人从一侧走进这条走廊,会发现走廊宽度仅允许一人容身,除了往前走之外什么都做不了,这是瑙曼为我们设置的压迫机关,虽然在他的其它作品中,压迫更多以一种无形的方式呈现。
在《小丑酷刑》与《人类学/社会学(旋转的兰德)》中我们会反复观看一个强迫式地重复尖叫与咆哮行为的小丑,一个不停旋转不停歌唱的歌剧家的头。瑙曼吸取了许多舞台表演和荒诞戏剧的表现形式,人物在经历残酷折磨的同时又以滑稽的形式呈现,当一个硕大的头颅在四周旋转时我们会听到循环播放的歌剧唱段,这种将人的精神与肉体同时置身于退无可避的境地的做法,会让我们联想到库布里克导演的电影《发条橙》中主角接受“矫正”的体验,也揭露了许多虚伪的现实。
“真正的艺术家通过揭示神秘真理来帮助世界。”瑙曼的霓虹灯广告写道。瑙曼向我们展现的是一种隐蔽的语言游戏,他用霓虹灯写出来的Run from Fear和Fun from Rear只差两个字母,存在、生与死、爱与欲望都化作霓虹灯闪烁的编码和强迫式的重复动作。当一句谎言被重复上千次就成了真理,那么一个词重复上千次会变成什么?那必将是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仅存在于我们身体内部的感触。语言能够表达得极其有限,唯有身处瑙曼的作品之中,才会对身体、语言与存在本身有所察觉。在本次展览中,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