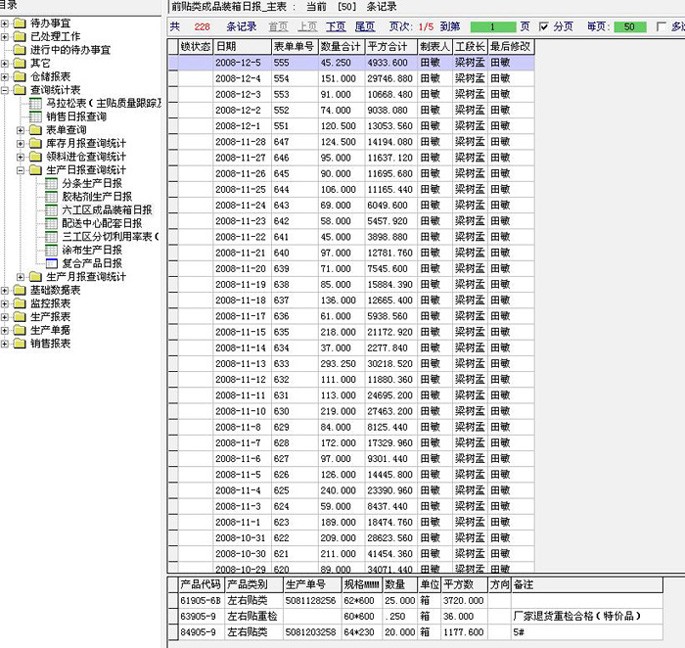2004年11月9日,美国加州,36岁的张纯如驾车离开了家。
 (资料图)
(资料图)
她的车辆一路驶出了城区,直到来到一处寂静、空旷的路边。两侧的道路荒无人烟,月光冷冷地照在地上,时间已经来到了凌晨2点。
车子缓缓停下,却始终没有人下来。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四下静默。突然,一声沉闷的枪响传来,巨大的后坐力让车身发出微颤……
同一时间,在远隔几十公里的家中,张纯如的丈夫发现了一封遗书:
“我走在街上被人跟踪,无法面对将来的痛苦与折磨。我的每一次呼吸都变得困难,这种焦虑堪比淹死在开阔的海洋中。”
“请原谅我。”
看信后,丈夫布雷特低声啜泣,他似乎早已预见了妻子的结局,尚在咿呀学语的儿子不懂父亲的痛苦,仍在挥舞着小手,喊着“ma ma……”
作为一名享誉世界的畅销书作家,张纯如用文字描述过无数次死亡,只是这次,杀死她的子弹,并不是署名Iris Chang的手枪,而是“来自67年前的南京”。
而她的命运,也早已与这座当时被西方世界禁言的城市,息息相关。
1968年出生于美国的张纯如,与南京大屠杀本没有任何关系。
她是华人后裔,父母都是哈佛大学的博士,毕业后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虽然从小吃汉堡、说英语长大,但张纯如的血脉里,流淌着对中国天然的亲近。
这都要归功于她的父母。他们从小就教育张纯如:“我们是被迫离开中国的”。
原来,31年前,侵华日军攻破南京城,大肆屠杀、凌虐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超过30万人无辜丧命。为了躲避战乱,他们不得不远渡重洋。
所以,张纯如从小就记得一个数字“19371213”,这是南京大屠杀开始的日子。
等她渐渐懂事,张纯如更能理解父母的痛苦:故国难回。心中有对侵略者的恨,还有对受害者们感同身受的悲恸,以及自己无法为他们做点什么的无力感。
她像海绵一样吸收着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信息,直到父母将自己的故事全部讲完。
她决定去更大的地方寻找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可即使是普林斯顿市的公共图书馆,也找不到一星半点对南京大屠杀的记载。她努力查找没有记载的历史资料,在其他人眼中,就像一个“异类”。
张纯如被弄糊涂了,她不明白,为什么一件人类历史上罄竹难书的罪恶事件,竟遭到这般“冷遇”?
她的困惑在美国高中历史课上得到了解答,人们激烈地讨论着奥斯维辛给犹太人带去的灾难,可几乎没有一个人记得,或提起骇人至极的“南京大屠杀”。
曾经,有一位历史学家估算,如果把南京死难者的手连接起来,足有200英里长,相当于从南京到杭州。流的鲜血达1200吨,尸体可以装满2500节火车车厢。
可是,这段浸满鲜血的历史,竟然被一些西方学者轻飘飘地“隐去”了。
张纯如越深入了解,便越发心惊,那些在“南京大屠杀”中犯下滔天罪行的刽子手们,至今仍不肯承认事实真相,对受害者们连一丝歉意也没有。
她的心狠狠地绞在一起,抽搐着,像被插入一根刺般难受。
张纯如常常在工作间隙中想到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切。
她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为美联社和《芝加哥论坛报》供稿,固定的新闻套路让她筋疲力尽,等到放假回家,看到父母头上新添的白发,她不禁胆战心惊。
“如果父母也老去了,自己会不会是世上最后一个知道南京大屠杀的人?”
于是,她拼尽全力寻找南京大屠杀的史实材料,结果却收效甚微。面对西方社会的避而不谈,张纯如只能将目光投向14000公里之外,大西洋彼岸的中国。
她的心中生出一种隐隐的期盼,这里的同胞必然和她一样,怀着怕这段历史消逝的忧思。
1995年,27岁的张纯如从报社辞职,开始为撰写《南京大屠杀》寻访中国。
这段旅程注定不轻松,短短25天时间,她每天在被称作“火炉”的南京工作10个小时以上,搜集整理资料只是一部分工作,更重要的,是要找到还活着的受害者。
她穿着临时从旅馆借来的雨靴,在泥泞的乡村小路间穿梭,曲深里巷里面,她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费尽千辛万苦,终于见到了满面风霜的幸存者们。
但是,当看到他们脸上死一般的寂静时,张纯如的心沉了下去。
她不忍将他们再次拉入几十年前的噩梦中,可又不得不硬着心肠,靠着对还原真相的信念支撑着自己,问出一个又一个让人落泪的问题:
“你还记得当年发生的事吗?”“你的胳膊是如何受伤的?”“他们强暴你了吗?”……
听到这些问题,他们才又有了反应,恐惧着、啜泣着,重新像一个活生生的人。
张纯如好像亲眼看到了,新婚的妻子被当成畜生般对待;刺刀挑起了母亲腹中的胎儿;一颗头颅被安放在木墩上;还有无数平民被推向屠场,浇上汽油,燃烧……
这些超越人类认知的事情,就真实地发生在面前的人们身上。
历史的断壁残垣中,人就像一粒尘埃般渺小,但生命怎么能承受这么多的痛苦与绝望?光听一点点讲述就觉得受不了的往事,是他们亲身经历的人生。
张纯如的眼泪浸湿了笔记,整整两大本,没有剩下一处空隙。
丈夫布雷特常说,张纯如把自己卷进去了,卷进这场人类浩劫中。
从南京带回来的资料,堆满了房间,十来个受害者的采访资料被放在最上面,张纯如每每拿起,都要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直面这人间惨剧的冰山一角。
南京大屠杀变成了她的梦魇,回忆、照片、人像,每一个都提醒着她:“快点记录”。
她没日没夜地对着电脑码字,感受受害者曾经经历的痛苦,在历史真相一次次挑战良知底线的折磨中,迅速地衰老下去。
哭泣、对着白墙发呆,还有无时无刻不在的心悸,死死地缠着她,不眠不休。
这个过程实在过于漫长,张纯如只觉得,每码一个字,就像从心底剜出一根刺,上面沾满了血,直到敲下最后一个句号,心彻底空了。
厚厚一沓的手稿,被寄到了出版社,《南京大屠杀》终于问世了。
15万字的内容,字字泣血,揭露了西方一直以来“隐去”的真相,在满是人权谎言的西方历史中,撕开了一道口子。
她详细地描述了日本人是如何有计划地实施了入侵,又在何时何地实施了何种暴行,包括强暴、虐待、凌辱中国平民,直至杀害他们。
这样宏大而具体的叙事,在历史书籍中很少见,很容易引发读者共鸣。
果然,在出版后的第二天,《南京大屠杀》就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并长居10周之久,无数的人蜂拥进书店,只为一睹这本书的真容。
还有很多人驻足在《南京大屠杀》的巨幅海报前,发出“Jesus(上帝保佑)”的感叹。
他们拍着胸脯,庆幸这样的厄运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同时又对书中的人们产生莫大的同情,南京大屠杀不再是张纯如一个人的事,而成为了所有读者共同关心的事。
这种改变让张纯如稍感安慰,她早已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她的背后,站着三十万同胞。
“作为一名作家,我要将这些遇难者从遗忘中拯救出来,替那些喑哑无言者呼号。”
所以,这当中的一切不适、痛苦,她都能够忍受,并下定决心,要继续战斗下去。
张纯如对未来的估计没有错,从把稿子交出去的那一刻起,敌人就接踵而至。
他们在网上给她泼脏水,造谣她是个“骗子”,称《南京大屠杀》一整本书都是骗局,更有好事者跑到张纯如的线下签售会上闹事。
这一切没有吓倒张纯如,她无比诚恳地告诉自己的读者:
“如果我出生在那个年代、那个地方、那个时间,我也会是其中的一具尸体,一具无名的尸体。”
而对于狠戾的挑事者,她勇敢地说道:“我没有听到‘道歉’的字眼。”
即使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公开对她发表声讨,她也不肯后退半步。
在她心里,对敌人的软弱,便是对死去的三十万同胞的背叛,是不能给受害者们讨回公道的失信。
她的心装满了死去人们的哀嚎与冤楚,沉重到让她喘不过气来。
和布雷特结婚的第11年,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克里斯托弗。可就在不久之后,儿子降临的欢喜变成了对未知的恐惧,一封装有两枚子弹的信件寄到了她的家中,寄件人匿名。
张纯如第一次感受到了害怕。
她不仅是个作家,更是个妻子、母亲,而现在,那些因为《南京大屠杀》爆火,而准备采取行动的刽子手们将枪口对准了她的家人,让她闭嘴。
她被冰封的内心,再次受到了重重一击,只是这次,足以致命。
2004年11月9日,她吻别了克里斯托弗,趁着丈夫布雷特酣睡时,悄悄驱车驶离了家。
她不知道自己将去往何方,只是副驾驶上的冰冷的手枪提醒着她,一切都将结束了。
睡梦中的克里斯托弗粉嘟嘟的小手张着,仿佛是知道了妈妈的选择,在做最后的道别。
张纯如死后,整个华人圈都被震动了。
无数的人猜测她是受到了威胁,甚至遭到了杀害,可是,加州的警方只在张纯如的车里找到她的DNA组织,而她的致命伤正是来自车里的手枪。
丈夫布雷特在得知张纯如出事的消息后,始终不肯接受现实。
2019年,张纯如公园在美国圣荷西市揭幕,参与赞助的有社会各界人士,在她的纪念碑上,铭刻着“挚爱的妻和母亲,作家,历史学家,人权斗士”等字样。
同年,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人们怀抱《南京大屠杀》一书,在张纯如的雕塑前静默、肃立,“请英雄回家”。
而这一切,张纯如都已看不到,唯有遗像中,她的笑容温暖而坚定,仿佛对“善”必将战胜“恶”充满信心。
如她所愿,《南京大屠杀》一书,在西方掀起了一场历史革命,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而那些死去的,或者等了半辈子的人们,终于可以放下心来。人间正道,虽迟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