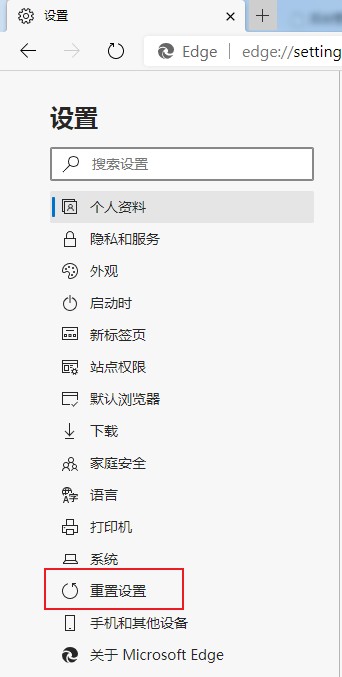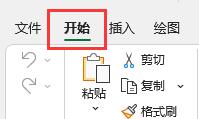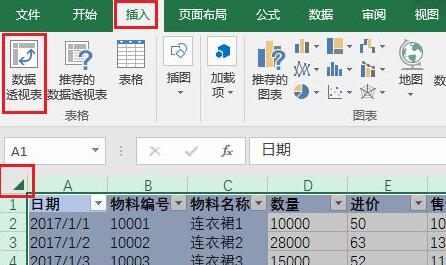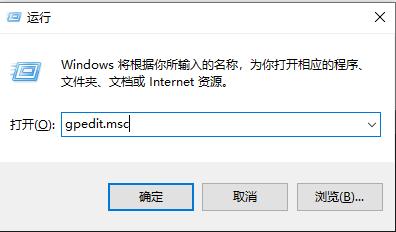今天推荐一本小说《莫须有》,作者是倪湛舸,北大高材生,芝加哥大学神学院宗教与文学博士,现为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宗教与文化系副教授。《莫须有》是围绕南宋“莫须有”冤案,以岳云、赵构、秦桧、岳雷的第一人称视角来进入同一段历史的六篇小说,作者将史料化为清晰可感的叙事,在既定的历史框架下再现了不同人物的幽微心理。感兴趣的网友可以买一本实体书来看看。
 【资料图】
【资料图】
今天继续分享。
十一 转了个大圈
丁捷果然是个骗子。高宠怎么可能是英雄,他稀里糊涂地死在了郾城。
战场上死人太多本不是什么事,但陈粟临走的时候忽然提起乱军中被投石砸烂脑袋的伙头兵,我竟哇地哭出声来,就像是多年前被小米哥按住被高秃子敲打的那次。我们在郾城跟兀术的主力军遭遇,他们没占到便宜便转攻颍昌,我爹派我领兵驰援,他们又没占到便宜,眼看着金人疲乏,我们收复汴京有望,官家那里却送来了退兵的诏令。
我哭是因为要离开的其实并不是小米哥而是我爹的北伐军。陈粟留在河朔投奔他那些义军朋友,这与其是他的决定,倒不如说源自我爹的恳请。陈粟原想跟着我爹撤回江南,继续做忠肝义胆的马前张保,我爹却铁了心赶他回去做山贼。陈粟不肯,我爹便劝他:“你想揍女真人,我也想。我被捆绑住手脚,你却不必。你留下继续联络义军,女真人要是找老百姓的麻烦,你们就打,省得我远水解不了近渴干着急。”陈粟还是不乐意,我爹劝累了,开始骂他矫情,于是换我陪他。
再其实并不是我陪陈粟而是他来看我,颍昌之战后我死猪似的睡了很久,究竟多久我也不清楚,陈粟说三天三夜那我就姑且信他。我没觉得自己伤得有多重,就是太累,累得根本睁不开眼,连做梦都是接连梦见自己在睡觉,就像从山崖上往下掉好不容易触了底结果身下又开始崩塌于是再次往下掉,反反复复掉了又掉也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能抬起身子冲着满脸忧思伤怀的陈粟哼哼:“小米哥,我好饿。”
干粮自然是有的,陈粟也没忘告诉我高宠死了。我委屈地哭了起来,那意思是你就不能等我缓过劲来另行施虐?
陈粟看出我的心思赶忙解释:“我就要走了,不对,你们就要走了,不赶紧跟你讲,以后谁还记得蒸包子的高秃子?”
我哭得更委屈了,不光高秃子死了,就连小米哥都要走,不对,是我们要往回撤,没粮草没援军外加死伤惨重,我在颍昌拼命打退兀术全都白搭了。
陈粟又做回山贼,岳家军退守鄂州,大家都是转了个大圈,回到原地。也许丁捷并不是个骗子?我们曾问他未卜先知料事如神到底是咋回事,他哼了一声:“我瞎算,不准的。不过神仙不用算,都说天上一日人间千年,神仙要是无聊了,就撅着屁股看人折腾,好比我们无聊了,就撅着屁股看蚂蚁打架。神仙一眼看过来,我们这里就是好几十好几百年光景,他们什么都看在眼里,当然什么都知道。啥,为啥神仙不来主持人间公道?你会在乎两伙蚂蚁打架谁正谁邪?你吃饱了撑的啊?”
所以啊,叫作高宠的蚂蚁被砸烂了脑袋也是不会有人在意的,还有更多我叫不上名字的蚂蚁被碾成了粉齑,饿得前胸贴后背的我果然没有气力多想什么。我还活着,谢天谢地。可在神仙眼里,活蚂蚁跟死蚂蚁想必也没太大分别,我哭着哭着,忽然明白哭也没啥用,只能擦干眼泪翻身下床去找我爹。我爹以北伐为执念,他又脾气暴躁,平生最恨半途而废,退兵这事,他断然不能泰然处之,我怎么可能不担心。陈粟拦我,说是我爹吩咐他照看我老老实实喝粥吃馕:“就你那榆木脑瓜能想通的道理,你爹还能不明白?”是啊,我爹什么都明白,只是有些东西,他放不开也根本就不打算放开。
陈粟走的那会儿暴雨如注。晌午过后天上就慢慢堆满了黑云,先是呼啦啦地刮风,又有一层层鸽蛋大小的冰雹往下砸,等到沉甸甸的雨水把远近的城郭都搅成一团泥浆,来接陈粟的人方才赶到。这就是早些时候跟着他渡江的那群义军,连同那匹被抛弃在渡船上的马。我爹叫陈粟拿些铠甲兵器走,还给了他面军旗,他骑来北伐的马也继续跟着他。
风雨实在凶猛,我本想与陈粟的义军朋友叙旧,却根本张不开嘴,他们打着手势道了谢才去抱起堆在地上的铠甲、弓箭和环子枪。陈粟牵着这匹马的缰绳去摸那匹马的鬃毛,拍完那匹马的屁股又来与这匹马头碰头,左拥右抱不亦乐乎。该死的女真骑手作战都有两匹马可替换,陈粟可算是体会到了那份奢侈。我双手合拢在嘴前喊他,怎么使劲都不够响亮,最后灵机一动扯着嗓子叫张保,他终于听见了,隔着厚厚的雨帘向我挥手。
大家都是落汤鸡的狼狈模样,小米哥却还是那么好看,眼睛乌黑,腰杆笔挺,就连浸透了雨水的破衣烂衫都不失整齐妥帖,他从怀里掏出个东西举过头顶给我看——那意思是你这礼物我可宝贝了——只见天地间的雨都急着奔向这方砚台,化作蝼蚁命中的浓墨重彩。
十二 三只猴子
我回到鄂州,终日垂头丧气,张敌万觉得我可怜,就钓鱼给我吃。我感激他仗义,陪他盘腿坐在江边钓鱼。他叫我挖蚯蚓做鱼饵,我想都没想一口回绝,被伺候的滋味真好,我还没享受够。张敌万哼着新学的小调骂我,这么多年了,他不管学会什么歌谣都要改了词来骂我。我才不跟他一般见识,他钓鱼,我打坐,把心里头乱七八糟的杂念一丝一缕地揪起来往外扔,让空洞还是那个空空的洞,让自己这块铁疙瘩能勉勉强强飘起来。
绍兴七年我爹跟官家赌气,带着我在庐山东林寺住了好久。他听和尚讲经,我学和尚打坐,他早就看穿我只是借机睡觉,可又奢望我梦中得道,于是睁一眼闭一眼。后来他被官家派来的人劝回建康,索性把我扔给官家算是放任自流,我跟着官家从建康去了临安,在临安憋闷了一年多光景,好不容易回到了鄂州,好不容易等来了北伐,结果倒好,转了个大圈,终于又能盘腿打坐借机睡觉,恍然不知身在庐山上,还是长江边,庐山上有和尚拿戒尺敲我脑袋,长江边的张敌万更狠,拿鱼竿抽我的背疼得我眼冒金星。
“你气力这么大,怎么不跟我去抓兀术?”我跳起来抢他的鱼竿,鱼线连着还没来得及收到筐里的鲫鱼,眼看着就要落回滚滚波涛。
“那你怎么不跟你爹去淮西抓兀术?”他一通手舞足蹈好不容易才把猎物又攥在掌心。
我们在北边的硬仗没白打,兀术退回老巢窝了小半年,开春后才又蠢蠢欲动,他不敢来长江中流,便去攻打淮西,官家调我爹去援助,我爹说那里没有骑兵的用武之地,把我甩在鄂州,吩咐张敌万陪我解闷。
丁捷和其他几个工匠被韩世忠借去修战船,整个冬天都不在,开春后也没消息。张敌万在城里的酒楼帮工,闲时只能拿我解闷,边钓鱼边跟我讲从商队那里听来的海外诸蕃国奇闻逸事,说天竺人拜的神仙浑身靛蓝,大食国的精灵殷红似火,海上的彩虹是活的长虫,船只被它吸进肚里是莫大的福分,那虫的每节身子都是一层寰宇,船上人漂流在三千大千世界,乐不思蜀更无心饮食,最后全都慢慢笑着饿死,先是剩下满船的白骨,后来连船都烂成铁屑木碎,满船的货倒是完好,若是海上风雨大作,那便是彩虹虫在吐这些俗物,把它们沉到海底再也不见天日。
“呸呸呸,我还等着你挣钱回来给我们发军饷呢。”我知道张敌万跟我爹要了本钱正在进货,等到丝绸瓷器茶叶都齐全了就要沿江而下,是真的准备出海了。他倒是什么都不忌讳,想怎么胡说八道就怎么胡说八道。
我们回到家吃红烧鱼,他吃光了上面的肉伸出筷子就要翻身,我赶紧打他的手
背:“你缺心眼吗?”他一脸不耐烦地吐刺:“在乎这些有用吗?世事要是真有定数,我是个什么熊样不也是定数?”
我卸了鱼骨头,他若无其事地继续吃,听他这么说我又愣了,张敌万究竟是谁的魂灵落进了这副皮囊?
反正是谁都行只要不是自己的张敌万继续没头没脑地说:“你等着,别看我打不过你,我要去南毗国抓两只猴子回来养,取名叫作敌百和敌千,我们仨一起揍你。”
我目瞪口呆:“你要认猴子当哥?”
他边吐刺边唠叨:“我又寻思着,还是把敌百和敌千放了吧,敌万已经生作敌万,敌百和敌千却不必做敌百和敌千,猴子嘛,就该回到山里野。”
我只恨自己眼睛生得不够大瞪不死他:“你还没抓到猴子呢就要放了?”
其实我爹也信算命,他知道丁捷不敢说啥,就去问东林寺的和尚,得知自己福薄,承受不起高官厚禄,顿时觉得辞官上庐山才是他的人生归宿,为此才迟迟不肯回建康,结果惹恼了官家,那是绍兴七年的事。十一年春,兀术在淮西转了一圈,仍旧没占到便宜,灰溜溜地滚回去了。官家自以为调兵卓有成效,把我爹和其他人都叫去临安论功行赏。我爹想起和尚的话,认定官越高祸越大,长吁短叹不肯动身,张叔叔开导他:“赶紧去,别再惹恼官家,这样辞官才有希望!”我爹只能又把军营托付给张叔叔,为报答他的苦劳,带走了我和张敌万两张大嘴巴。我是官家指名道姓要他带着的,张敌万打算去淮东找到丁捷拉他一起出海。
“你俩有个任务。”我爹瞥了一眼人模狗样的我俩,脸上一点得意的神色都没有,“路上闭嘴。”
十三 哭哭笑笑喘口气
我爹话少,大半时间都在冷眼看人,剩下的工夫用来低头想事。他年少投军屡建奇功,麾下兵士越来越多,官也越做越大,这次去临安,官家给了他个枢密副使的头衔,还赐了座宅子给我们住。我得跑腿置办东西,卷起袖子扫洒也是我的分内事,忙里忙外腰酸背痛不说,偷闲坐在门槛上啃个桃子望个天都会被我爹数落。
“讨厌临安!”我狠狠地再咬一口果肉,被酸得龇牙咧嘴,“我要回鄂州!”
临安是行在,官家住这儿,还有一堆唧唧歪歪的大臣,他们围着我爹和另外几个来论功行赏的武将一通吃吃喝喝,结果武将倒是升官了,他们手下的统制却全都直接听命于官家了。简而言之,我爹调不动鄂州的张叔叔他们了。兵权没了,打个鬼啊。我爹无事一身轻,换了身文绉绉的衣裳去找韩伯伯喝茶,扔我在空荡荡的新家里待着练字。我想不明白自己为啥要来临安受罪:我爹生闷气,我更是憋得慌,我俩大眼瞪小眼何苦呢?
问起为何又带着我,我爹一脸无奈地答:“要怨就怨官家去,我也不明白他怎么总惦记着你。”被官家惦记害得我浑身不自在,我爹看我愁眉苦脸,索性抬脚就走,他反正潇洒得很,有湖光山色怡情,有韩伯伯陪着喝茶聊天,眼不见为净。既然他都出门了,那我也往外跑,去百花巷找智浃,谁知跑遍了那一带的茶楼书场都不见他的人影,倒是街头刚说完书正在数铜钱的吴三娘子一眼认出了我:“小衙内回来了!我总惦记着没看够你!”
我讲不好故事,却最会听故事。智浃说他就喜欢我这样的看官,安安静静地躲在角落里,该笑的时候赶紧发笑,该惊的时候知道受惊,遇见伤心事大家都伤心欲绝,我也照本宣科地伤心。“你这双眼睛生得特别,被你盯着,我就忍不住地掏心挖肺,想把什么都讲给你听。”智浃感慨,“难怪你身边有那么多朋友。”
我在临安只有智浃这个朋友,特意出来找他,不承想他听说我爹来了临安,特意登门拜访,两边生生走岔了。智浃没找到我,留了字条,我爹见我居然结交了读书人朋友,甚是欣慰,说要请他来讲解春秋左传。
给人泼冷水想来是我的能耐:“他不务正业写话本。”出其不意是我爹的能耐:“那更要请!”
其实吧我爹也爱听说书,他喜欢三国,尤爱关羽。我听书好生投入,把心思全都揉进别人的悲欢离合,自己跟着跌宕起伏死去活来,可说书人话音一落,我就跟睡醒了似的身子一震,那些个缠绵悱恻荡气回肠梦魂般纷纷散落飘逝,镜中本无花,水里何曾有过月。
我爹不一样,他偶尔听闻些忠义故事,就牢牢记在心里,每每念叨起来,说自己也想要做英雄。小时候的我满眼热忱地问他英雄是个什么东西,他却笑笑避而不谈,急得我直跺脚。急也没用,我都二十出头了,我爹还是会偶尔说起做英雄,原先的语气还算激昂,而今却倦怠多于嘲讽。
临安四月,柳色青青,我爹看着好风景也没心思,私下跟我抱怨:官家好不容易捡了这皇位,仰仗着群臣辛苦经营这些年,终于有了这套还说得过去的家业——他怎么可能舍得拿出去跟女真人硬碰硬。朝里盘根错节的都是些江南士族,他们也犯不着为了跟自己不沾边的北方流民出头。君臣都想议和,我们打退了兀术正好给他们筹码,现在卸磨杀驴的时机到了,赶紧辞官才能全身而退。只是苦了老家众人,没渡河的被女真人蹂躏,来了这里的流离失所勉强度日,还是苦不堪言。
“这临安城里的百姓,都爱听些怎样的故事?”我爹见了衣冠楚楚彬彬有礼的智浃果然高兴,高兴得赶紧直奔主题。智浃偷偷在背后向我比手势,怪我出卖朋友。我倒并不觉得过意不去,那是我爹啊,你们同我讲什么不就是告诉了他?智浃毕竟是大方之人,心里并没有高雅低俗的障碍,把市井趣味讲解得如同六经般庄重。他反问我爹是不是爱读经史,我爹实话实说爱读却不甚懂,他便笑言书场里有说经的也有讲史的,这经是佛经故事,这史是前朝兴亡。说经讲史固然风行,可更还有那银字儿和铁骑儿。银字儿是配着小曲的故 事,演绎男欢女爱、舞刀弄棒、神仙灵怪。寻常百姓终日操劳,就指望靠这些哭哭笑笑喘口气。可如今乱世,大家心里太苦,竟嫌银字儿轻巧,就都催促着说书的说铁骑儿,岳枢密去年的征战故事谁人不爱,都有书会编排出了直捣黄龙的好结局!
“要是能让大伙儿哭哭笑笑喘口气,也就够了。”我爹伸手拍飘到他肩上的柳絮,“功名尘与土啊。”
十四 跟我走
“讲故事的人和听故事的人心里都憋屈,都找不着地儿出气,就指望着故事里的英雄尚义任侠,那还是太平年头。如今战乱,大家都恨女真人,就最爱大破金兵的故事——韩世忠的黄天荡水战,吴玠吴璘苦守仙人关,还有你爹大破拐子马铁浮屠——这些都是说铁骑儿的看家本领,满城的老百姓想到金兵就担惊受怕,在自家地盘上艰难度日又吃苦受气,只有躲进这些士马金鼓之事图个痛快。”
智浃说得如此头头是道,我便不依不饶地追问:“那我去哪里图痛快?”
他生了张枣红脸,脸再红也看不出:“哎哟衙内啊,我知道这世道害得你也憋屈,要不领你吃酒去?”
我摇头:“不去。你能编个故事让高宠当大英雄吗?”郾城颍昌我们虽胜了,但伤亡惨重,后来又匆忙退兵,活下来的幸运儿都觉得对不起回不来的倒霉蛋。要是伙头军高秃子能在智浃的话本里当大英雄,那小骗子丁捷也能翻身继续做神算子。
智浃满口答应:“你想要高宠有多厉害?”
我想起木勺敲头的惨痛往事:“比我还要厉害吧,岳家军最强战力就是他了。”
智浃上下打量我:“那你做个白袍银甲的英俊小将?”
我知道他见我穿白有心发挥,赶紧把头摇成拨浪鼓:“打仗穿白?我有病吗?”
平日里我总是乱穿些颜色灰暗的粗布衣裳,上战场的军服是深红色,来临安后被逼着换成素净的白衣,我爹说白衣不耐脏,只要乱跑乱动就会一目了然,这分明是挖空心思管制我。我讨厌白衣就跟讨厌临安一个道理,讨厌临安与讨厌官家也是一回事,十五岁那年跟着我爹来临安见官家穿的就是束手束脚一身白,难受得好比坐牢。我也渴望自己是个别的什么人的魂灵,只是暂且困在这副皮囊里,假以时日,我不再是我,就当是老天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先前独自在临安憋着,现在跟我爹一起憋着,要不是舍不得他,我倒真想跟张敌万和丁捷一走了之。五月里我爹跟着张俊去淮东帮韩世忠整顿军队,回来时带着张敌万和丁捷,他俩在海州盘桓数月出入船坞,这会儿来临安等海船装完货就走。
智浃急着尽地主之谊,提议带大家去西湖赏荷花;张敌万不领情,非要去钱塘江边看官家逃命用的船队。智浃早就从我这里听了许多张敌万的奇闻逸事,知道他除了长得还算周正,整个人就只能用旁逸斜出漫无边际这种词来形容,所以见怪不怪,路上只管细细打量张敌万和丁捷,跟我的粗略描述比较一番,看能不能用三言两语把这俩的鬼样给勾画出来。他说张敌万是个机灵鬼,见人就笑,笑起来眼睛闪闪亮,下唇还往外努显得特亲切。
至于丁捷,他跟人说话喜欢压低头上的斗笠不想被看见脸上的神情,那双手还不老实,幸好有斗笠让他又摸又拽化解尴尬。我同智浃讲,那不是尴尬,丁捷漂泊惯了,跟谁混都心不在焉,既然飘然世外,就得自己想办法找点乐子。
我们这里忙着臧否人物,张敌万和丁捷也没闲着,一会儿嘀嘀咕咕一会儿四目相对,张敌万没少叹气,丁捷也破天荒地抬起斗笠远远望我。他俩是在担心我,因为淮东那里差点出事。
有人告发韩世忠的亲校谋反——张敌万一到临安就噼里啪啦地向我通报险情——韩世忠的亲校!就好比你爹身边的小米哥!就好比有人要害小米哥再整他身后的你爹!还好你爹听闻传言赶紧叫我跟丁捷跑去给韩伯伯报信。我俩谁都不是啊所以没人防着啊再加上跑得快又嘴皮子溜啊!
丁捷向来说张敌万的反话,这次却赶紧接茬:老韩吓得赶紧快马加鞭赶回临安求官家,你爹不紧不慢办完事才带着我们过来,我们来了才打听到老韩仗着先前救过官家躲过一劫,可这都什么事啊太吓人了,云哥儿跟我们走吧?
张敌万点头如捣蒜:就朝廷这粪堆,我们又不是苍蝇,犯不着往上扑。韩伯伯为啥求官家管用?我看这事原本就是官家的意思!
嫌弃西湖是个臭水坑却非要跑来钱塘江边看船队,张敌万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警醒我这个不开窍的。你看看你看看——他把手背在身后仰面吹风——时刻不忘自己逃命,宁可给这些闲置的船只披金戴银也不愿多发些军饷,为了自己大权在握更是什么腌臜事都做得出,就这种东西,我向他讨饭都觉得丢脸,哪怕只有个小舢板我都要出海挣钱,我张敌万偏不受这窝囊气。说到慷慨激昂处,他情不自禁伸手抓我:“云哥儿,跟我走!”我苦笑着挣脱他的手掌:“干吗,去讨饭?”
十五 颠倒妄想
海上没遮没挡,日光劈头盖脸地往下泼,撞上汹涌的波浪又被往上抛,于是加倍毒辣,丁捷这种见不得光的怎么活?丁捷对我的关怀不以为然,说自己是属耗子的,白天在船舱里窝着,天黑才上甲板透气。张敌万更是笑我杞人忧天,他那意思是,丁捷要是老老实实待在鄂州,过的不也是这种日子,坐船出海虽苦,却能见到不一样的世界,何乐不为?
我想了想,还真是这么回事。丁捷向来活得昼夜颠倒,白天要睡到未时才肯起,每到深更半夜,别人都东倒西歪,他却点着根蜡烛读《易经》《葬书》,调息观想他也干,掐手诀剪纸人那些邪门歪道他也玩,总是忙得不亦乐乎。我爹原先想收他做亲兵,也是觉得有他守夜放哨挺好,只可惜水战近年里像是打不起来,别说水战了,朝廷又开始同金人和谈,骑兵都赋闲着,还不如学陈粟落草为寇。
住在临安我家的新宅子里,丁捷果然还是昼伏夜出,大半夜溜进伙房吃剩饭剩菜不说,还拿到院子里同翻墙进来的野猫分享。张敌万想看十几只野猫陪丁捷吃饭的盛况,拉着我爬起来看戏,可他嫌那些猫全都是歪瓜裂枣,没一只像样的,蹲了片刻就失望地跑回去睡觉了,留下睡不着的我跟丁捷一起评点丑猫——这个瘸腿,那个缺耳朵;这个斑秃,那个断尾巴;这个脏得看不出毛色,那个太凶,见到谁都哈气——果然全都不堪入目,难怪张敌万跑得快。
“两位衙内是有追求的人,不像我,看到这些丑猫才觉得亲切。”丁捷啃完了冷包子正搓手,“属耗子的我,比它们还不如呢。”
我想起我爹打听的事,自己也的确好奇,便问丁捷:“你跟过程昌寓,也跟过杨幺,现今同我们混在一起,这么多年来,找你算命的都是些怎样的人?”
丁捷双手撑着双膝仰面转头,也只有在月光下,他才能舒展开身子:“四方亡命乐纵嗜杀之徒啊,大伙儿格局都差不多,烂命一条凑合着过,达官贵人的八字我怎么看得到。”
我坐在他身边,拿膝盖碰他膝盖:“神棍哥,我的烂命到底是怎样的?”
丁捷赶紧挪开身子:“献殷勤也没用。我劝你跟我们走,你不会放在心上,这就是你的命。要是能改得了躲得过,命还是命吗?”
我知道他又想避开这话题,索性单刀直入:“你明知道高秃子烂命一条,为什么说他能成为大英雄?”
丁捷扑哧一声乐了:“我造口孽啊,我就是胡说八道,该怎么报应我都认了。但你别小看这胡说八道,一念发动,无论虚实,都是因果,既是前因的后果,又是后果的前因。
我说高秃子是大英雄,就好比推了个雪球下山,等着它越滚越大越滚越大……”
“可是,这雪球跟高秃子有什么相干呢?”
“那你说,你的命跟我们的命相不相干?”
被丁捷反问,我使劲想了想,想得脑壳生疼——陈粟留在河北做山贼,张敌万丁捷就要出海远航,只有智浃留在临安,他们各有各的活法,让我羡慕不已,就好像自己凭空多出好几条命来。我看不清自己的命,却把这些别人的命都看在眼里,看得好生投入,就好像他们都在为我活着,用自己的命编成一张网把我层层套住。我们谁都不会独自沉到水底,因为我们的命彼此交织彼此牵挂。所以,我们也能把高秃子捞起来?
野猫吃饱了,躺了一地,满意地打起了呼噜。我像是明白了什么。丁捷看我这副恍然大悟的神情,得意地趁热打铁:“你再琢磨琢磨,既然一花一世界,雪球到底是什么?”
我竖起耳朵细听厢房那边传来的呼噜声,那是张敌万。他不想做自己,也不想活在这个屎坑一样的世界,他想去全然陌生的地方,他不会在任何地方长久停留,如果可能,就连三千大千世界他都想看遍,如果可能,三千大千世界里,总有那么一处属于大英雄高宠,既然我们这个世界原本就是颠扑不破的颠倒妄想,丁捷随口说出的颠倒妄想又何尝不能成为另一个颠扑不破的世界?
“口孽可凶了!开辟鸿蒙,掌管生死……”丁捷跟着遍地野猫一同呼吸,他的眼睛也像猫,滴溜滚圆,瞳孔色若琥珀。
“可是,此时此刻,我们又能如何?”想到暗潮汹涌的朝廷,想到岌岌可危的我爹,想到自己又被困在临安,我顿时泄了气。